内容提要
從王樹人先生提出的象思維出發,深入探讨和比較了中西文化的超越類型、學術取向,以及關于普遍性、客觀性的不同層次、内涵,中西科學傳統的不同類型與發展道路,提出中國不同于西方的本體論、實踐論、價值論學術體系。建議在象思維與中國學術體系的基礎上,總結中國古代科學規範,重建中國科學史。主張在學習西方科學的同時,緻力于喚醒中國科學精神與原創性,開辟中國科學自主創新之路。
關鍵詞:象思維 概念思維 生命 生成 自主創新
西學東漸以來,從中國有無宗教、有無哲學,到有無科學,圍繞中西文化的比較和争論風雲激蕩。目前,中國有無科學再次成為争論熱點。王樹人先生(老樹)提出的“象思維”問題,基于中國“道通為一”之高境界、大視野,從文化之活的靈魂——思維方式着手,對于中國文化傳統正本清源,繼往開來,可謂是一種突破。這一突破,主要表現在繼承和發揚徐光啟提出的“會通以超勝”文化觀。由此出發,不僅對于中西文化乃至科學的根本差異給出了統一解釋的可能,為中國科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方法,也為人類思維的健全發展指出了新的出路。
一、象思維與中西思維方式的會通
何謂象思維?根據《回歸》一書及《中國的象思維……》等文規定,中國的象思維是一種動态整體的悟性思維,與西方概念的理性思維不同,它是一種“非實體性,非對象性,非現成性,富于原發創生性”的思維方式。(1,(三)3,) 從思維發生史上看,比起理性的邏輯的概念思維,悟性的“象思維”是具有更加本源性和創造性的思維。”它“是人類文明最終的創造性的思想根基。” 而中國文化經典,“主要是訴諸象思維”而創造的。(3,P1,9)
語言文字是文化之根,思維方式則是貫穿整個文化發展過程的活的靈魂。中國的象語言與象思維,決定了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質,從而也決定了兩種文化一切相應領域——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的根本差異與不同的曆史發展道路。今天,随着時代的發展,如何從中國文化的根源出發,振興中國文化精神,開辟中國文化與科學的自主創新之路,已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内在需求。
但是,如何走進中國古典文本呢?如何承接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精神與生命智慧呢?對中國學者來說,這一本應不成問題的問題卻隐含着深刻的曆史困惑與文化危機。由于近代以來西方中心論思潮的沖擊,中國已發生嚴重的文化斷層。文革以後,我們開啟了西學之窗,而國學之窗卻依舊封閉。目前情況雖有改觀,但嚴重的問題是,不僅我們的教育體制和知識層面全盤西化,而且我們“在思維方式上也幾乎全盤西化。”中國“獨具原創性的象思維“幾乎被“完全遮蔽甚至‘集體失去記憶’”。以緻許多人解讀和诠釋中國的傳統經典,也隻會用概念思維,語言分析了。如此,不僅古意盡失,而且“非離譜不可”,不僅難于走進文本,甚至會歪曲和肢解文本。老樹提出的問題,振聾發聩。
反思我們今日之思維方式,不僅對“象思維”失去領悟能力,同時對概念思維亦不得其源。如此,我們究竟複興什麼文化?自主創新之“主”在哪裡?
實際上,目前圍繞中國文化與科學的種種“有”“無”之争,隻有從中西文化的思維方式與價值根源出發,在曆史、現實與未來人類發展的大視野下,才可能正本清源,厘請思路,我們也才可能為中國文化與科學的存在找到合理的依據,并發現中國文化不可替代的世界意義。然而,文化精神的失落,不僅成為我們正确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的障礙,也已成為我們正确理解和吸收西方當代哲學與科學優秀成果的蔽障。如果說,“回歸事情本身 ”,“懸置概念思維從而煥發人的想象力,在人類文明發展和創造的曆史中,永遠居于最本原最重要的地位。”(2,P4)那麼,重新認識“象思維”,探讨中西思維方式的會通,就不僅對中國文化複興,對中國科學的自主創新,而且對整個人類文化健全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二、兩種思維方式下的超越類型
追根溯源,“中西思維方式的本質不同“首先表現在“最高理念之不同。”(3,P3)文化的最高理念是超越現實命運的形上追求。軸心時期,中西文化幾乎同時完成從命運到境界的超越,但古希臘從最初之自然哲學,到柏拉圖,亞裡斯多德,“其最高理念皆表現為外在實體。”(3,P3)從将命運看作鐵的邏格斯,到信仰絕對外在的彼岸上帝,西方基于概念思維,其“哲學的突破”是“外向型超越”,這種超越的主要特點是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分離。“超世間是世間一切價值之源,它不但高于世間,并且也外在于世間。” (4,P10)從此,西方主流文化便“在‘主客二元’的大框架内”,沿“實體性、對象性、現成性”之思的形态發展。特别是近代以來,斯賓諾莎的上帝與獨立于人的客觀世界的預設,始終是指引西方哲學與科學探索的基本信念。
而中國文化從語言文字開始,即與西方分道揚镳,軸心時期的先秦,無論周易之太極,孔子之仁,老莊之道,其最高理念皆可歸結為具有“原發創生性”的“道”。 (1,緒論;3,P3) 中國人通過“觀物取象”、“象以盡意”,一開始就試圖在整體流動與轉化中理解和把握自然(自然而然)之“本然本真”,他們從将命運看作生滅之過程,到追求與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參,以達“道通為一”之最高境界,其“哲學的突破”乃是“内向型超越”,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統一,正是它區别于其他各大文明的顯著特點。(4,P12)從此,中國主流文化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沿“非實體性,非對象性、非現成性”之思的道路發展。而“格物緻知”,“道法自然”,“明心見性”,最終入德而悟道,則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古典科學所信守的最高理想。
顯然,雖然中西文化皆緣起“象思維”,并幾乎同時完成對經驗或感性直觀之超越。但中西文化超越的方式、層次和宗旨卻大異其趣。曆史的事實是:西方文化基于“音象”而走向概念思維之路。這種思維方式主要是通過邏輯定義、判斷、推理、分析,而将感性經驗提升為抽象理論與公理化體系,旨在以普遍形式之理解釋經驗現象,獲得關于外部世界的确定知識。其思之所及,一切皆為實體性的既成對象,故必然走向主客二元,心物對立之發展道路。可謂由“抽象”而“著象”,離于經驗而落于經驗。而中國文化則始終基于“形象”,堅持“象思維”發展方向,試圖超越感性經驗乃至“名言”(邏輯理性)之思,旨在“得意忘象”或“遣志蕩象”, 趨達“大象無形”“天人合一”之境界,獲得生命覺悟之“德性之知”。其思之所及,宇宙萬物皆在“整體流動與轉化”中,故必追求 “主客雙泯”、“物我兩忘”之境域,可謂由“取象”而“破象”、乃至“超象”,基于經驗而超于經驗。我們認為,就超越的層次與境界而言,西方的超越是有限的,不徹底的;而中國的超越則是“帶有根本性的。”徹底的。
必須注意的是:中西兩種思維方式所側重發展和體現的人類能力及心智所用是不同的。它們各有短長,偏于任何一方都必造成曆史的缺失。注意到“‘象思維’是人類所共有的本原性思維,是前語言前邏輯的思維。”(1,3)但随後,西方之邏輯思維有充分之發展,象思維則隐退不顯。而相反,中國之象思維有充分之發展,并由前邏輯而達超邏輯,然其概念思維卻不發達。可以說,西方基于感性經驗而崇尚理性,中國則注重生命實踐而崇尚悟性。這種悟性,如牟宗三先生所說“智的直覺”,或“理性直觀”,可謂一種更高層次的理性。或許,我們可将概念思維與象思維看作理性在不同層面上的表現,它們體現了不同的文化精神。
必須承認,對現代世界的建構,概念思維更為有效。經驗問題的确定、解決以及清晰的表達,需要概念思維,然而一切原創性想象力,卻離不開象思維,兩種思維方式本應是互相學習,相互補充的。值得注意的是:從概念思維到象思維,或從象思維到概念思維皆非直推的關系,其間沒有邏輯的通道。但它們亦決非對立的關系。老樹多次強調:從概念思維到象思維,必須有“懸置”或“放下”的功夫,而從象思維到概念思維,則必須發大心立大願,為解決現實社會問題,接受和運用概念思維,有所建樹,有所創新。(參1,3)
近代以來,西方概念思維下兩大知性構架——民主與科學,成為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關鍵,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卻“矯枉過正”,将中國文化與民主科學對立,緻使我們的思想始終在“西化”與“國粹”兩極震蕩。盡管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的優秀學者未曾放棄過中西會通之努力,但尚未深入涉及思維方式問題。“象思維”的提出,無疑是當今中西文化會通中的一種突破, 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講通中國文化與民主科學兩者之道理,以求其内在之貫通,有機之統一。此即是落到中國文化生命之根裡,去尋求去成就民主與科學。故無論從道理上或從中國文化上,皆要求我們對于理性之兩種表現有一種貫通的說明。”(4,P100)而今天“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問題而言,”“特别需要‘象思維’與邏輯概念思維會通。” 需要對西方與中國文化的雙向溝通與揚棄。
三、兩種思維方式下的學問體系
兩種思維方式的深入比較與會通研究,為中西學術或學問體系(包括科學)的不同取向與發展道路,兩種學術體系中基本原則與規範的核心,提供了内在原因與統一解釋的可能,也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功過利弊與曆史作用。
概念思維的實體性,對象性,現成性以及外向超越特征,決定了西方學術的理性的認知取向。近代以來,西方主流文化進一步肯定并強化了‘主客二元’‘靈肉二分’原則,建構并日益完善了以“存有論”(ontology)、認識論、方法論為主幹的西方文化哲學體系,形成宗教、哲學、科學三大支柱鼎立的近代西方文明。直至二十世紀,在西方主流思潮中,試圖将天與人,主與客,心與物聯系起來的說法都被看作是荒謬的,錯誤的。因此,“在西方哲學裡,視講生命的哲學不是正宗的,亦不是真正的學問。這是因為他們把生命與理性對立,不能在這裡開辟出真實的學問。”(6,P25)而概念思維的長處,賦予西方學問體系嚴密的邏輯性與理論的系統性,認識的構成性、确定性、清晰性及可操作性,最适于工業時代的需要,造就了西方近代社會的發展與科學的輝煌。而其最大的問題,則在于人與自然的對立,理性與生命的割裂,以及認知與價值的隔離。近代以來,盡管西方人“船堅炮利”,稱霸全球,而終于在精神上“失去了家園”。
中國的象思維及内向超越特征,則決定了中國學問的實踐性“價值取向”,直至西學東漸,中國主流文化始終在“天人合一”或“主客一體相通”大框架内,緻力于開顯成聖、成仙、成佛之生命實踐與自然大道,以本體論、實踐論、價值論三位一體,創立了獨具風格的的生命的學問體系,在曆史的發展中形成儒、道、釋三家為主的中國文化格局。
我們認為,象思維作為動态整體之思,包含“中道”思想。因而,保證了主體與客體,形下與形上的貫通性,中國的學問體系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人與天(自然),人與神(或佛),乃至人與萬物,都是一體相通的。同時,象思維就其表現為生命之思而言,必然是價值内在的。由此,若以中國學術規範為标準,一切将兩者割裂的說法,恰恰都是不究竟的,不通的。而一切背離價值的“法術”,都是無本的,非正當的。《周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老子的“生成論四因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五十二)(13,P80-81)一開始就将價值引入了對自然的理解,一開始就以“道”“德”為萬物生成之根源,這裡,不是上帝,而是自然最高之“善”——天道,天德(亦稱“大德”“玄德”)保證了萬物之“生生不已”。
由此,中國之學問,乃是“生命的學問”,它“直下是人生的,同時也是宇宙的,所以本源是一,而且同是德性意義價值意義的。因此,從宇宙方面說,這本源不是無根的、随意猜測的,這是直接由我的德性實踐作見證的。同時從人生方面說,這德性意義價值意義的本源,也不是局限而通不出去的,故性與天道一時同證。一透全透,真實無妄。無論從宇宙論說下來,……或是從人生說上去,“皆是兩面不隔的,亦不是不接頭的。”(7,P120)
此外,與概念思維不同,象思維之“象”,并非隻是可見聞之現象,而是從現象出發,層層超越,從外象到内象,從客體到主體,從表象直至本然本真之“原象”。與之相應的“觀”與“思”,亦與西方那種生命外在的感性直觀與概念之思不同,無論《道德經》之“觀妙”“觀徼”“觀複”之“觀”,還是《金剛經》所謂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一體同觀”之“觀”,都是傾注全副生命的“觀照”,都是包含感性直觀在内的實踐性“動态之觀”。就此而言,象思維不是西方理性之思,而是生命體驗之悟性之思,它本身就在生命實踐的過程中,或本身就是生命體驗。
綜上所述,無論是西方的或中國的學術傳統,都是在曆史的長河中逐漸演化而生成,各自完整自洽。而象思維與概念思維的差異,決定了中西文化在不同曆史時期的不同作用與命運。在概念思維下,各學科分門别類,有相對獨立與充分之發展,但亦造成隔行如隔山之片面性。而在象思維下,學科界限不明,文史哲不分,雖有相通之利,但缺少專業之獨立發展,亦造成見林不見樹之模糊性。顯然,較之概念思維,象思維更具本源性,但未必更落後。從整個人類思維發展看,象思維與概念思維是相反相成的,正如太極之兩儀,此消彼長,此顯彼隐。“中國與歐洲各自沿着自己的曆史道路前進,無論從大處或小處看,本來應該是不成問題的。”(5,P5)
然而近代以來,在西方話語霸權下,西方文化的原則與規範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準,以緻象思維“幾乎被完全遮蔽”,而中國文化的“存在”及其價值則一再被否定和消解。譬如,中國文化中的本體,乃指人之根本,而形而上,則指成形之前,中國的本體論與形而上學原本都是關于其最高理念 —— “大象無形”之“道”的學問。無論道家之“無物之象”,還是佛家之“實相一相,即是無相”,都旨在破除對“物”、“我”的執著。将西方基于實體的ontology譯為本體論,基于物理學的 metaphysics譯為形而上學,本為不妥,進而以西方ontology與metaphysics為标準,反而批判中國沒有本體論,沒有形而上學,乃至沒有超越。中國文化精神的失落與“失語症”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四、兩種普遍性與客觀性之内涵與特征
今天,在西方中心論思潮下,許多人仍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普遍性和客觀性,并由此斷言中國沒有科學。實際上,從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學問體系出發,普遍性的含義、範圍和層次也是不同的。
概念思維以人類感性、知性與理性的普遍存在,為邏輯理論建構的先天條件,其所達到的是形式的普遍性。概念思維通過定義,分析,将事物規定在有限的範圍内進行研究,其确定性,清晰性是以犧牲整體性、生命性為代價的,而一切形式邏輯所作的論證,其适用範圍都是有限的,因而必然是不完備的,排他的。
而中國之象思維則以道德本心或人類良知的普遍存在,及其與本然之“天道”、“天理”合一,為實踐的先天依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所達到的是“道通為一”的普遍性。首先,象思維中的“定義”方式,皆非實指定義,而是劃分定義,這種定義給出的是“一個大方向的能指”而在這個大方向下的“可能的所指是無限的”。(2,P3)正如《周易》“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顯然,“無論是内涵還是外延,象思維都大于概念思維”。(2,P3)故能“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其次,象思維作為生命實踐之思維方式,基于經驗而包容經驗,它不僅是普遍的,而且是完備的。所謂:“夫易廣矣大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周易》)特别重要的是,中國先人已洞察到語言與“名言”的局限,深知“道可道,非常道”;人類一切争鬥,“首先産生于這個‘知與言’”而唯有“超越世俗之境界和視野 ,站在‘道通為一”的高度,世間的一切差别和對立”才可能“融于大道而被化解和超越。”(2,P7-8)乾坤之大和諧需要“自強不息”而“厚德載物”的精神。顯然,象思維比概念思維更為圓融,其特點恰恰是創生的不确定性與普遍性、包容性。
兩種思維方式下,客觀性之含義亦大異其趣:概念思維下的客觀性,是以主客二分為前提的。近代以來,西方科學始終有一難解之謎,那就是認識如何能夠超越自身去有把握地切中客體?科學的所謂客觀性,始則以完全獨立于人的客觀世界的存在為依據,認識論轉向後,又以主體間性,經驗有效性等為依據,至建構主義,SSK則幹脆抛開客觀存在,僅僅歸結為主體建構,甚至社會集團的利益需求。顯然,這種知識論上的所謂客觀真理性實際上是片面的,不可靠的。因此,在西方哲學史上不斷受到诘問、懷疑甚至否定。此外,基于對實體的形式與質料的靜态分析,西方科學有形式客觀性與内容客觀性的二分,故其數學可獨立于經驗或實踐而發展。
與西方不同,象思維之客觀性以天人合一,主客不二為前提,以宇宙萬物之本然本真為依據。 它要求“緻虛極,守靜笃”,通過“心齋”“坐忘”而緻“吾忘我”,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由此體悟自然之大道。因此,不是知性的的客觀性,而是實踐的客觀性。正如西方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說:這種客觀性“必須排除所有會在對物的理解和陳述中擠身到物與我們之間的東西。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沉浸于物的無僞裝的在場。”(8,P9)進而,象思維要求“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以物觀物”,而不是人為自然立法,“以我觀物”。(《周易》)其客觀性,不僅僅要求與現象相符,而是追求“彌綸天地之道”的終極客觀性
然而這種終極客觀性亦存在現實的難題:由于“道通為一”的境界是一無限追求的過程,而具體社會中的人們隻能處于這一過程的不同階段,因此,在經驗世界,便缺少統一的評價标準。此外,象思維所把握的是整體的流轉與變化,故不可能給出具體的确定規則與操作程序,必須具體情況具體處理,顯然,這裡缺少的是“主體間性”所規定的“認知”客觀性。
總之,中西關于“客觀真理性”的内涵與層次不同。張世英先生曾提出“真”有不同的層次。(詳見9)我們認為,從人類追求真理的全過程看,終極的“存在之真理”與經驗世界“知識論上的和科學的真理”本為不可或缺的次第與終的。而終極客觀性正是科學客觀性的形上根據。“ ‘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種至大的明澈境界,此境界決非人力所為;相反地,人唯有首先進入此境界中,而後才能與物相對待,而後才能‘格物緻知’,才能有知識論上的和科學的真理。”(8,中譯本序 PⅢ)
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第一流的哲學家、科學家已認識到概念思維的局限,而對中國文化與科學情有獨鐘。目前,正由于西方天人分離、主客二元所造成的“客觀性”難題,以及科學的價值中立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态破壞等危害,探索主客統一的可能,以及如何将價值引入科學,已成為科學哲學關注的話題。而随着系統科學,認知科學的發展,西方科學思潮亦開始由原子構成論走向生成整體論,這一切,正推動西方試圖超越經驗科學,探索實踐科學之路。中國的象思維在經過百年的沉寂、反思後,必将以新的面貌重登曆史舞台,對人類文化與科學的未來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五、不同思維方式下的科學形态
“科學”,science一詞源于西方十七世紀,最初由special轉義而來,含義為專門與分科之學。牛頓創立經典力學,波義爾确立化學時,也隻有“自然哲學”,并無所謂“科學”。如今,究竟什麼是科學,依然聚訟紛纭,或許,這正說明“科學”乃屬于人類實踐的曆史範疇,其自身的發展總是不斷突破原有定義的限定。
如果我們将科學看作人類認識自然,探索自然界普遍規律的活動,以及在此過程中創立的知識系統,而不是以西方近代科學為唯一規範或标準。那麼,不同的思維方式與學問體系,産生不同類型與發展道路的科學,應是合乎邏輯的。
顯然,西方近代科學是概念思維最顯精彩和特色處,文藝複興後,繼承古希臘原子論及其邏輯、數學傳統,借助當時中國技術成果,西方人以其勃發的創造性和自由精神,發揮了實體性、對象性、現成性思維優勢,完成了理性與經驗的結合,創建了近代機械論科學。以牛頓力學為範例,逐漸形成以物質為基石,堅守主客二分、價值中立,以還原論為方法論原則的近代科學規範,并發展出一套公理化數、理體系與可控實驗系統,促使西方迅速實現機械化,并将整個人類推向了工業時代。“武器的批判”幾乎擊敗并遮蔽了所有非西方文明的“科學”及其成就,從此,西方近代科學成為人類探讨自然規律的唯一标準與普世真理。
然而,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科學已開始轉向,相對論、量子力學,特别是系統科學的興起和發展,已使西方科學發生重要的規範轉換,原來的“小賽先生”成長為“大賽先生”。科學的世界圖景,由無生命的原子或機器,轉變為系統的生成過程。面對前所未有的難題。許多西方前沿科學家已看到概念思維的局限,貝塔朗菲曾指出:“我們主要關心可度量的質,可分的單元,可能是由印歐語系所決定的。… 我們的思維方式明顯地不适合處理整體和形式(形态)問題。” “處于别的文化中的人類…,可能有根本不同類型的'科學。”(10,P236,238)
與西方近代科學不同,中國古代科學恰恰是象思維的典型産物。可以說,它是另一種形态的生成整體論科學。首先,它肯定宇宙萬物都是從無到有生成的,過程是根本的。世界上不變的唯有變化本身。其次,它選擇最符合象思維的非實體性的“氣”為世界之物質基礎。而物質隻是氣的凝聚。由此,天地萬物的運行,乃是一“氣”聚散生化的無窮過程。“氣”有象而無形,不可指之為實,但可征之以象,中國古代科學所把握的,乃是在“氣”的“整體流轉與變化”中萬有生滅的普遍規律,而不是靜态的物質運動與構成規律,亦非對象性實體的生成規律。如将生成演化分“氣化”與“形化”兩階段,中國古典生成論根本在“氣化”,而當代西方系統生成論本質為“形化”。中國古代科學基本模型——陰陽五行正是典型的生成論“氣象學”模型。(14,P23-25)最近,劉長林先生提出中國以“意象思維”與“象規律”為基礎的“象科學”(詳見17),亦揭示了中國科學傳統基于“象”這一關鍵。
實際上,中國古代科學以天學、數學、中醫學、農學等為代表,在長期的發展中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規範,它在價值取向下,堅持天人合一,主客不二原則,以實踐的感應論或感通論為基礎,建立了一套數學機械化或程序化算法體系,采用“觀物取象”,“取象比類”方法,“尚象制器”,“開物成務”,使中國古代科技在十五世紀前遙遙領先。正如李約瑟所指出:“有人以為中國人的成就都是在技術方面,不在科學方面,實則不然。”“在上古與中古時代的中國,就有一大套自然主義理論,就有系統的,有記錄的實驗,有一大堆準确得令人驚奇的測量工作。”(11,P63)特别今人驚歎的是,中國古代工程技術,如都江堰,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順應自然,利用厚生,妙用自然力,充分體現了“象思維”的智慧。
顯然,中國古代科學與西方近代科學,由于思維方式不同,自然觀不同,因此所關注的層面與發現的規律亦不同。在器物制造方面,西方科學的定量化比中國古代科學更精确、更清晰,在經驗層面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檢驗性。而在生命的整體把握方面,中國古代科學則更有智慧。其合理性與有效性是無可否認的,不僅國人有目共睹,而且已獲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承認。認為中國科學不準确,不清晰而加以否定的說法是片面的。正如海德格爾所指出:“一切精神科學,甚至一切關于生命的科學,恰恰為了保持嚴格性才必然成為非精确的科學。”“那種認為現代科學比古代科學更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無意義的看法。”(9,P77)
目前,關于諸如“取消中醫”等問題,正如美國著名科學史家席文所批評:“實際潛藏着一組導緻災難的假說。它們所以會導緻災難,是因為它們鼓勵我們除了現代科學最直接淵源于其中的那個科學探索之外,對其他的科學探索都不是盡力按照其自身的條件去加以充分理解而是去妄加評價。”(12,P107)我們認為,中醫正因基于生命的動态整體性,不可還原而完全定量化,正因其非機械的特性而難以把握。如果說中國古代科學有所不足,關鍵問題當在缺少知性構架。我們的責任正在如何改進與完善之。
中西科學差異集中體現了兩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在此根本差異下,中國古代生成論科學與西方近代機械論科學是互斥互補的,與西方當代系統生成論科學是相似相通的,不可能也無須“一方吃掉另一方”。如何從正确體悟中國科學的基本精神和理論出發,給出其現代诠釋,如何根據其本身規範,整理出一套經驗層面可操作的規則,以及有效的檢驗标準。更重要的,如何繼承中國科學思想而有所創新。确實需要中西思維方式與文化各層面的大疏通。盡管我們已有著名數學家吳問俊等人的突破,但作為整體文化的複興,尚有待人心之“大回向”,有待整個民族“原發創生性”精神與能力的崛起。
六、探索中華科學自主創新之道
放眼世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包括史學在内,顯然已開始轉向,實證主義(以自然科學為範本)、文化一元論、和西方中心論都在逐步退潮之中。相反的,多元文化(或文明)的觀念已越來越受到肯定。”“中國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終于會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預設之一。”(5,P6)
面對又一次世界性文化綜合浪潮,我們不能不問:今天,我們要與世界接什麼軌?我們以什麼與世界接軌?難道中國今天的自主創新以取消自身文化與科學傳統,而僅以模仿西方傳統,解讀國外文本、依賴他人原創為自豪?難道中西比較唯以宣布中國落後或一無所有為能事?
我們認為,關于中國科學史的研究,應按中國本身的曆史,思維方式與學問體系重新清理、認識而進行重建。中國的自主創新,當力求“會通以超勝”:一方面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之精華,“翻上來從根上滋生我們的指導觀念。”從而“疏導出科學的基本精神,以建立知識方面的學問統緒。”(15,P53)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向西方學習,吸收西方文化與科學的優秀成果,認清世界發展大勢,于當今人類需要而尚未解決的難題,有所突破,有所貢獻。于人類未來的發展,有所開拓,有所創新。老樹提出的“象思維“及其思想,無疑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與新的思路。本文僅就思之所及,提出以下初步建議:
一、重新闡釋與古希臘原子論不同的以周易、道家、陰陽家等思想為基礎的中國自然哲學。
二、重建或創建以“本體論、價值論、實踐論”學問體系為基礎的中國科學哲學。(區别于西方以 “存有論、認識論、方法論”為基礎的科學哲學。)
三、重新清理并提出非實體性、非對象性、非現成性,從而具有“氣象性”、生成整體性與貫通性的中國科學基本理論與體系。(區别于西方“實體性、對象性、現成性”科學理論與體系)
四、整理并提出與西方科學還原論不同的生成整體論的方法論原則。闡明從象思維出發,悟性與實踐結合,運用“象數邏輯”,以實踐體驗與檢驗為主的中國古代科學研究方法。(區别于西方從概念思維出發,理性與經驗結合,運用數理邏輯,以實驗觀察與檢驗為主的研究方法)
五、總結并提出中國科學關于自然生成的基本的普遍規律及基本模型。
六、提出與西方學科論分類體系不同的中國本體論分類體系。(詳見16)
七、研究并提出中國古代科學的成功範例(如天學、中醫藥學),特别是當今中國自主創新的成功範例。如吳文俊先生在數學上的突破。(詳見18)
八、介紹以中國古代科學為基礎的“尚象制器”之技藝與“道法自然”之工程技術。
李約瑟的研究證明,中國古代至少有“震動世界的十項(或十二項,或十三項)發現或發明。”這些發現自有其理論基礎。作為中國科學的重建, 正應該“不但要指出這些發明的來源,而且要指出古代的科學理論研究是如何産生這些發明的。”(11,P64)
顯然,中國科學的重建與自主創新是一項巨大的曆史性工作,或許需要各個領域幾代人的努力。然而,我們認為,隻有從根本做起,循中國曆史本身之内在線索,深入研究,才可能提出不同于西方科學的中國科學規範與科學體系,中國科學史的研究才可能确立自己的話語系統,理論根基與研究綱領,彌漫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上空的迷霧才可能廓清。由此,中西科學比較才有平等可言,中國科學創新才能基于自身之原創而有真實之自主。
總之,文化是一整體,在未來的發展中,中西文化需要科學、哲學、宗教等各種層面的對話、交流和會通,中西文化與科學隻有走向互補,才能充實健全。如圖簡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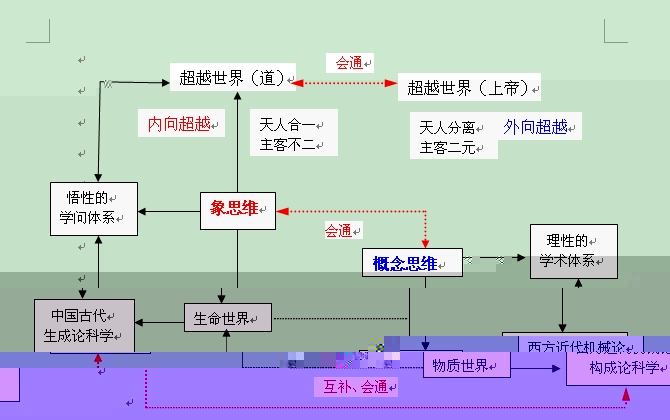
不難看出,思維方式是文化的核心問題。“象思維”的再發現,無論對今天的中國文化研究,還是中西文化會通,都是一件大事,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科學雖為現實世界之事業,但與思維方式及思維境界不可分,“我們必須重視科學背後那種超越的精神”,“如果不具備“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西方)科學是不會在中國生根的。”(5,P500) 而如果沒有“象思維”及其“道德創造性”,中國科學傳統亦不會有真實的現代生命。今天,除了科學成果的學習、研究,中國科學精神的覺醒與重建,中西科學精神的會通與互相激勵,當為科學創新之根本前提。實際上,正如老樹所指出:象思維作為一種“原發創生性”的思維方式,“即使在當今時代裡,在悟性的“象思維”已經被異化形态的理性和工具理性遮蔽的情況下,這種悟性的“象思維”也作為文明發展的思想根基在不動聲色地發揮作用。”(3,P9)
鑒于長期以來,我們(包括筆者)多以近代科學規範為标準,運用西方邏輯概念思維方式思考、研究、闡釋與評價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難免牽強附會、削足适履,甚至邯鄲學步,數典忘祖。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取得很大的成績與進步,但如何“會通以超勝”,實猶任重而道遠。針對中國文化被邊緣化,“原創之思”淡薄與缺失的現實,老樹才竭力呼喚“回歸原創之思”,作為中國學者,隻有在深知本國文化的基礎上,才可能走向世界。(參見1,自序,P1-2)面對全球化浪潮,盡管中西文化與科學的交流、對話會有許多不同的方式、途徑與層面,但正本清源,促進概念思維與象思維之銜接、互補、會通,全面健全我們的思維方式,實為中國文化與科學自主創新的根本之道。
參考資料
1、 王樹人:《回歸原創之思——象思維視野下的中國智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王樹人、李明珠:《感悟莊子——象思維視野下的〈莊子〉》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3、 王樹人:《中國的象思維及其原創性問題》《學術月刊》 2006第1期
4、 餘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 2004年版
5、 餘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 2004年版
6、 牟宗三主講《人文講習錄》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版
7、牟宗三《生命的學問》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版
8、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9、張世英:《現實、真實、虛拟》 《 江海學刊》2003年 第1期
10、[美] 馮﹒貝塔朗菲:《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 》林康義等譯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87年版
11、[英]李約瑟《大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範庭育譯 帕米爾書店 1984年版
12、[美] 席文《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 是否沒有發生?》 轉引自李國豪等編:《中國科技史探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中文版
13、李曙華:《生成的邏輯與内涵價值的科學》 《哲學研究》2005年 第8期
14、李曙華:《中華科學的基本模型與體系》 《哲學研究》2002年 第 3期
15、牟宗三:《生命的學問,說懷鄉》 轉引自《牟宗三集》黃克劍等編 ,群言出版社 1993 年版
16、孫關龍:《先秦自然國學的集大成者——〈爾雅〉》《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 第5期17、17、劉長林:《中國象科學觀:易、道與兵、醫》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2007年3月版
18、吳文俊:《吳文俊論數學機械化》 山東教育出版社(濟南) 1995年版
--------------------------------------------------------------------------------
*李曙華:女,1949年出生,現為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科學思想史,系統科學、生成科學(emerging science)及其哲學問題,中西科學思想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