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最後兩位同學,已是深夜十時許。甯海路與北京西路交叉口的燈光依舊明亮,過往的行人卻已稀少。他們行色匆匆,是離家遠行呢,還是急着回家,這我就不得而知了。隻有随風飄落的梧桐葉,倒讓我感到秋的到來,這是真切的。
我一直認為,秋天是石城最美的季節,即便是最傑出的詩人也無法描摹其一二。而秋映入心,總是不免有愁的情緒,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心随境轉”罷。是故當所有的老師和同學互道尊重而散去,相握的手心尚留着餘溫,我的内心不免有些落寞,說不清是對青春的追惜,還是對離别的不舍……總之,一時是百感交集。
再過幾天,也就是10月18日,是我的母校——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百年系慶了。籌畫系慶的老師曾給我來電,讓我寫點回憶的文字。我一時欣然答應,但因雜事纏身,竟然沒顧上。現時想起來,覺得茲事甚大,母系百年華誕,于我們每位學子是十分榮耀的,雖就我本人了無成就可報,但略記往事而志喜是應該的。所以我索性籍此冷寂的時光,步行回家,讓自己的思緒如秋葉一樣随意紛飛。
我是1980年考入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本科的,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後招收的第四批大學生。我報考南大哲學系的因緣,是偶爾聽說南大有兩位名字中帶“明”的人物十分了得,一位是校長匡亞明,一位是哲學系老師胡福明。而我的名字中正好也有一個“明”,所以瞬時對南大哲學系有種特殊的親切感,填報志願時毫不猶豫将其作為第一志願。這由此讓我想起梅贻琦先生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所大學的著名學者,對莘莘學子來說,是最具吸收力的,當然也是最好的宣傳。
入得南大哲學系,通過四年的學習和生活,我感到我的選擇是正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43位同學,以不同年齡的成熟或青澀,操着帶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話,互相砥砺,讓青春激出本有的火花。而老師們從學習到生活的種種關懷,真正讓我們學以成人,為後來走上工作崗位打下了基礎。雖然我班最終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學并不多,但大家都從“哲學”一門裡獲得了智慧,并用于工作與生活之中。而這一點,可能是更有意義的。
南大現在的校訓是“誠樸雄偉,勵學敦行”,據說前四字是其前身——東南大學的校訓,後四字是蔣樹森先生任校長時加上去的。我們那時尚無校訓一說,但從老師的身體力行和校園文化中,能夠切實感受到一種獨特的風氣,這在南大就是創新、開放、包容、嚴謹的風氣。這種風氣至少對我們那一代的南大學子是有巨大影響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南大是最早推行學分制的,有必修和選修兩類,這給了學生根據興趣拓展知識有着極大的自由度。我自己就選修了法學、政治學、世界曆史、辯證邏輯、世界語、紅樓夢專題、音樂欣賞、美術鑒賞等課程,因為我的興趣點在法政和人文思潮方面。有的同學對科學哲學感興趣,故而選修了不少與理科相關的課程。還有一位同學,甚至還選修了與哲學專業看似極不相幹的機械制圖,而且學得極為專注,後來才知他是對計量經濟學感興趣,是為将來制作模型作準備。我佩服他的前瞻性,也開始相信世上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南大在當時也算得上是最早推行通識教育的高校之一,雖然當時還沒有“通識教育”的提法,但匡校長強調開設大學語文必修課(以王力主編《古代漢語》為教材),應該說是極具眼光的。當時我們這些踩着“文革”尾巴上大學的一輩,由于小學和初中階段的教學幾乎荒廢,語文(特别是古代漢語)的基礎其實相當薄弱,對古代文史知識、傳統文化典籍更近乎空白,所以這門課真正彌補了我們的不足。至于我們哲學系,蓋因“哲學”有“全部科學之母”或“科學之科學”之說,所以系裡開設的課程更多,甚至有高等數學、量子力學等,那原本是理科生的必修課,我們這些文科生大多敬而遠之,但也有個别學生竟學得津津有味。
開放和包容,我一直認為是現代大學的精神所在,這才能“學以成人”,也才能“開成創新”。在這一點上,北大由于蔡元培創“兼容并包”之旨,似乎一直得領風氣。而在我們上大學時,坦率地講,南大此方面的風氣是一點不弱于北大的,要不然不會出胡福明老師,甚至不會有孫叔平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學術公案,于此不論。至于在學生中間,理科生蹭文科的課,文科生搶聽理科的講座,在南大是一種常态。我本人就擠搶過數學家楊樂的講座,盡管對其專業懵懵懂懂,但知道還有别樣的世界和領域,頗開了眼界。
那時候,老師的教學是甚為精心的。在我的印象中,系裡除了孫叔平先生因年事已高、身體多病而沒有開課外,其他老師悉數為我們本科生上過講台。一些已在學界負有盛名的教授帶頭講,中年骨幹教師以及剛畢業的青年老師跟着講。往往一門課由多個老師講,大有趕學比超的意思,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老師講課的風格當然是各異的,因而有的課人滿為患,有的課甚為寥落。但再寥落的課,老師也沒有點名的習慣,這就是當時南大的風氣。我記得有一門課,最後隻留下三位學生,而我是其中之一,且有逃無可逃之感,但那位老師還是講得極為認真,大有“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慨。
當然,自由與嚴謹也是并行不悖的,這是一所大學的兩翼。南大的嚴謹和科學精神是自來由之,可追溯至其前身中央大學所創的“科學社”,我們說其是南大的标識也不為過。現在時常聽說南大比較“低調”,其意有褒有貶。褒者謂其學風踏實,不事張揚;貶者謂其不擅争先,缺少宣傳。我是始終從褒義角度看待這種“低調”的,可以說我自己也受此種“低調”風氣的影響。我一直認為,大學是以學術為本位的,學術體現在對知識和真理的求索上,秉持的是一種理性的态度,它不需要也不必要像賣糖葫蘆那樣高聲叫賣。如果放在一個百年甚或更長的時段看,那麼老校長李瑞清先生所說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恰是深得高等教育之三昧的。
由此再說回到我們的母系——南大哲學系,算得上百年滄桑。其有大師輩出的時代,亦有撤并沉寂的時期,改革開放後重現榮光,現在則繼往而開來,這是令每個系友感到高興的。如果說母校像家的話,母系則像寝室,它更是我們自由自在的精神樂園。所以我本人本科畢業後,曾經常回學校回系裡。更因着這份情結,我再次師從賴永海教授讀了博士學位,籍以重拾青春時光。而由于我一直從事出版工作,與系裡不少老師多有接觸,并有幸為他們的成果安排出版。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優秀的出版人在出版尺度上是不應有偏私的,但人總是有情感的,看着母系成果疊出、影響不斷擴大,心裡還是竊竊自喜。我想,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罷。
古語有“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我之投身南哲大門既非失足,故而無恨;學有四載,唯有感恩。所以在這次我班入學40周年之際,有同學要我寫幾句,我就随寫小詩一首:“天開教澤于鐘山,南雍重築讀書台;同窗四載相與嬉,再逢相問爾是誰?”
……
想着這些,原本略感涼意的身體,最終卻漸生出暖意來,而雙腳已不知不覺到了家門口。
家裡的燈還亮着。我想,百年南哲的思想之燈将會是更亮的罷。
2020年10月6日深夜于南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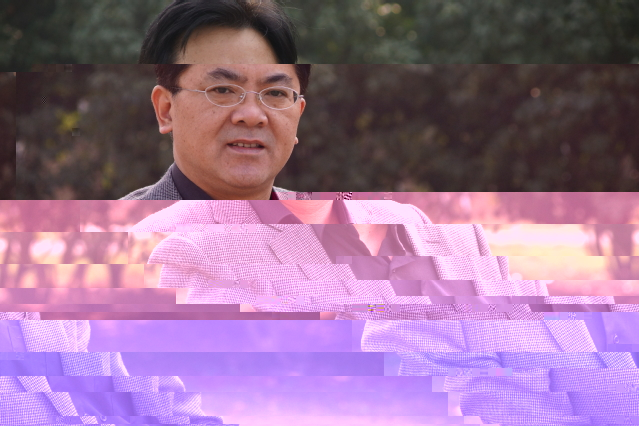
作者簡介:府建明,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80級本科生,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理事長、江蘇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